一“码”当先, 守好食品安全
“民以食为天,食以安为先”。食品安全,一直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。一袋馒头、一杯黑米粥……扫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,就能看到原料从哪儿来、生产批次、工艺环节等信息。如今,在食品加工行业,食品溯源体系应用越来越广泛,让安全有迹可循。消费者为何通过一块小小的二维码,就能了解食物来龙去脉?工业互联网是“核心武器”。近日,记者走进位于合肥的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,揭秘二维码背后的故事。工厂数字化,保障食品品质4月初,在青松食品加工厂门口穿上防尘鞋套,记者走进位于四楼的参观走廊。俯瞰车间,工作人员正在流水线四周忙碌着,这里看起来与普通加工厂差不多。“你看,门上方悬着的方形盒子,那是个感应器。”顺着青松食品信息化部总监闫猛手指方向,记者察觉到了不同。在加工车间和成品储藏间相接的门口处,隐约能看到设备运行的光亮。“这是MES制造执行系统,除了肉眼可见到的传感设备,在看不到的地方,流水线的机器也内置了感应模块,实现全流程的生产监控。”闫猛解释说,这几条生产线主要做包子、馒头一类的面点,面点经过的加料、发酵等环节是何时完成的,都可以用红外线等传感器记录下来,数据实时上传到服务器,最终反映在消费者看到的二维码上。据了解,MES制造执行系统搭建后,目前工厂在国内食品加工行业走在前列。为何要打造数字化工厂?闫猛跟记者分享了几段过往经历。“大家都知道面点需要发酵,发酵要控制温度、时间,一旦过头就废了。以前厂里就发生过,工作人员时间没掌控好,一批面点全部不能用。还有,中筋、低筋等面粉种类多,又十分相似,以前还发生过原料投放错的情况。”闫猛说,虽然产品都在质检环节截留,不会流向市场,但也造成了原料浪费。“现在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。发酵时间到了,设备就提示。工作人员投料之前,要扫描原料包装上的条形码,有了录入系统这个环节,不仅在管理上方便追溯,在生产过程中也多了一道把关。”水、电、天然气能耗统计图,车间生产进度,产出量与投入量对比图……在系统后台,记者看到一张张线形图。从依赖人力到利用系统管理,这些数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、保障产品品质。闫猛补充说:“通过纵向的对比数据,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效信息。比如,更精确地计算原料需求量,更及时地发现设备故障等。”全程可追溯,构筑安全屏障在生产厂房的一侧,仓库门口同样繁忙。一批新到的大米正从货车搬运下来,一袋袋大米整齐码放在托盘上。“滴!”仓储部工作人员许传存手拿设备,扫了一下托盘上贴着的条形码,接着输入标记在大米包装上的生产日期。“好了,可以拖到库里去了。”设备屏幕上显示着大米商品名、数量、订购单信息等。许传存说:“如果大米录入量达到了订单量,系统会提醒。”跟着货运架,走进仓库内部,几个立式货架高耸至房顶,实现对空间的最大化利用。记者注意到,每个货位上也贴有条形码。许传存说,货放到架子上,再扫一下架子上的条形码,就算完成入库了。等到取货时,只要找条形码就可以找到相应货物。在青松食品工作十多年,许传存一直从事仓储工作。“以前,货到了,先填单子,核对数量,登记入库。取货时,全靠记性找货在哪儿。一些量不大的货,很容易就忘了。货积压多了,甚至想找都找不到。再发现时,货都过期了。”他告诉记者,最麻烦的是如果团队里换了新员工,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。“现在有了这个WMS仓储管理系统,真的比以前方便多了,终于不用什么都靠脑子记了,还是系统更好使!”仓库有了“大脑”,对库存货位进行优化,把货物放在正确的地方,从而提高仓库利用率,可以有效分配劳动力,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,降低整体运营成本。因为主要经营短保食品,配送环节的安全和时效至关重要。青松食品对此也进行了数字化改造,保障货物更高效地送达。在其自有的100多辆货运车上,均装有定位系统。闫猛告诉记者,通过TMS物流运输系统,串联起发货、承运及收货,订单全流程实时可视。系统根据订单情况安排线路,再将订单分配给司机,就近配送,有效缩短配送时长和路途成本,完成后续的提货、送达、回单操作。互联网技术赋能企业的运输管理,从而提升了整个运输链条的效率。“系统可以随时查看订单状态,并抓取每个订单的轨迹查看是否发生中断或异常停车,保证配送过程中的安全。如果订单超过常规时间,会自动记录提醒。”闫猛补充说,这对消费者而言,也是一道重要保障。“基于配送环节的数字化,在溯源二维码中,甚至可以将配送时间、由何人配送等都告知公众。”活用数据库,赋能企业管理食品安全与民生息息相关,这就要求企业必须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来保证食品的质量,降低生产成本,提高竞争优势。通过MES等信息化手段,青松食品在业内率先建立完善的产品追溯系统,对所有原料、成品进行在线数据管理,实现产品质量的安全顺向可追踪,逆向可溯源,风险可管控,实现了从原料、生产、质检、包装、存储、运输、销售到食用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记录与追溯。一袋一码,消费者用手机扫描,信息即一目了然。“工作互联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生产上,在企业管理上,以ERP为基础实现订单、排产、配送、退货、财务结算、成本控制为一体的无纸化处理平台,减少了人工参与,方便业务运行,并节约耗材、人力成本,实现数据随需而查,流程高效严谨。”闫猛说,目前,已形成全面实时线上订单、时时提报、在线定位、统一调度、移动配送,实现内外信息互通的“五位一体”现代化企业管理格局。自2019年完成数字化改造,时间已过去2年有余。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来沉淀下来的数据?是青松食品近来考虑的问题。闫猛认为,数据为企业提供了可靠的決策依据。通过对消费者、生产、销售、供应商等信息数据分析,一方面可以形成消费者画像,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的产品;另一方面,可以优化生产链。“比如,我们的产品供应商每次交付的货品质量如何、准时与否,可以从数据中捕捉到,从而可以给供应商评定等级,再次优化。”加速传统产业迈入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,闫猛说,作为一家食品加工企业,食品安全永远是重中之重,用好信息化手段能让安全有迹可循。接下来,他打算在经营网点的管理上,尝试使用数字化手段。“不仅在成品的食品包装上有可溯源的二维码,还要让消费者在任何一个渠道上买到的食品,都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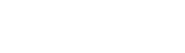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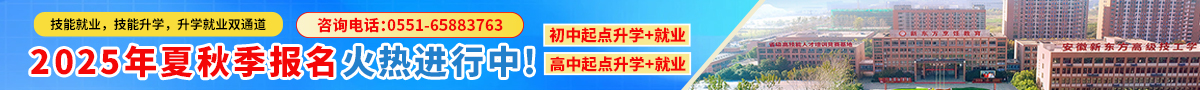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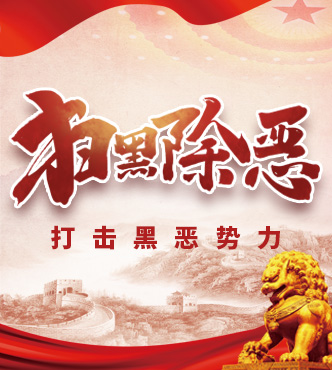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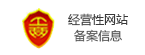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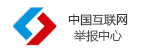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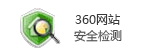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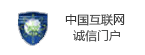
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1582号
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1582号